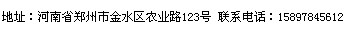众病之王15
从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实验中排除出这些对象相对很容易:放射线医师只需在X射线检查前简单询问其先前病史即可。但是由于对照组是虚拟群体,不能进行实际的询问,只能进行虚拟的剔除。夏皮罗尽量公平严谨地从实验的两组中剔除相同数量的妇女。但是,他可能还是不经意地作了选择,也可能是矫枉过正:更多已患乳腺癌的病人从筛检组中淘汰了。尽管区别很小:3万实验对象中只有位这样的病例,但在统计学上却是事关重大的。批评者指控说:“对照组中过多的死亡率只是人为挑选的结果。对照组被错误地纳入了更多的已患乳腺癌的妇女,这里面过多的死亡率只是统计数字的假象”。
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的热衷者震惊了。他们承认需要公正的再评估和重新实验。但是,该在哪里进行这样的实验呢?显然不是在美国——这里已经有20万妇女加入了乳腺癌筛检示范项目(不符合再一次实验的资格),而且学术界正对此争吵不休。整个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界在争论中茫然地蹒跚前进,进行过度的实验。他们不是在其他试验基础上进行有条理的再实验,而是发起了多项齐头并进、甚至相互阻碍的实验。年到年间,数量庞大的乳房X射线摄影试验在欧洲并行展开,分布在爱丁堡、苏格兰,瑞典的好几个地方:马尔默(Malm)、科帕尔贝里(Kopparberg)、东约特兰(stergtland)、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和哥德堡(Gteborg)。与此同时,在加拿大,研究人员自行发起了他们的随机化乳房X射线试验,叫作“国家乳房筛检研究”(NationalBreastScreeningStudy)。正像乳腺癌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样,乳房X射线摄影的实验转变成了一场军备竞赛,每一组都试图超越其他对手。
☆☆☆
爱丁堡地区一片混乱。在这里,数百个孤立、闭塞的医疗执业点星罗密布,这原本是一个很难开展试验的地方。医生们以近乎武断的标准将众多的妇女分派到筛检组或对照组。更糟糕的是,妇女们自愿选组,完全破坏了随机性的规则。试验进行当中,妇女经常从一个组换到另一个组,从整体上混淆了任何有意义的诠释。
但是,加拿大的试验却是精准和细致的典范。年夏天,一项大力宣传的全国性项目启动了:以信件、广告、个人电话访谈的形式,3.9万名妇女被招录进了15个经认证的医疗中心,进行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这些妇女来到任何一个中心后,首先会接受接待人员的初步询问,填写一份调查问卷,然后再由护士或医师检查,最后,她的名字将被记入一份公开的名册。医院都用蓝线条的记录本,自由流通,因此通过记录本上的行列交替实现随机分配。第一行妇女被分到筛检组,第二行的妇女就进入对照组,第三行再入筛检組,第四行进入对照组,依此类推。
请注意这些事件的顺序:通常妇女在被询问医疗史和做检查之后,才被随机分配。这个顺序不是事先设置的,也不是规定中的要求(指导手册细则已经发给每个中心)。但就是这小小的改变,使这个实验功效尽失。护士访谈过的分配已不再是随机的。乳房和淋巴结检查结果异常的妇女被过多地分到了乳房X射线摄影组(一个试验点中:有17人在筛检组;5人在对照组)。对于有乳腺癌病史的妇女也是如此。同样,基于过往病史和曾经的医保赔付申请的“高危”妇女,其分配也不成比例(8人在筛检组;1人在对照组)。
直到现在都没有查明发生这种倾斜的原因。是不是护士把高危的妇女分配到筛检组,通过乳房X射线摄影获取一个复诊意见来确认临床检查中的疑问?这样做是刻意破坏试验吗?还是,这只是无意识的同情之举,通过迫使妇女进行乳房X射线检查,来帮助她们?在候诊室里,高危妇女是否故意跳过候诊室的顺序,以求落入分配簿中向往的位置?实验协调员、检查医师、X射线技术人员、接待人员有没有指导她们这样做?
后来,流行病学家、数据统计员、放射科医生和至少一群法律专家曾组成各种团队,仔细地审视了潦草的记录本,试图解答这些问题,找出实验在哪里出了差错。实验的一位项目主持人反驳道:“怀疑,就像是各花入各眼,写在观察者的眼睛里。”猜疑四起。记录本上的抄写错误比比皆是:姓名的改动、身份的调换、被涂改液描白的行列,名字的替换或重写。现场工作人员的证词证实了这样的观察。在一个中心,一名实验协调员有选择地把她的朋友们集中到筛检组(大概是希望这样关照她们,帮助拯救她们的生命)。在另一个中心,一位技术员报告说:妇女们被“暗示”参加某个组,随机化普遍地受到了干扰。学术期刊里充满相互谴责的声音。癌症研究者诺曼?博伊德(NormanBoyd)在一篇概要评论中轻蔑地写道:“有一个教训已经很明显。临床试验的随机分组,应该以无法颠覆的方式确保实施。”
但是,除了这个惨烈的教训之外,其他依旧模糊。从迷雾中细碎显现出来的是比健康保险计划还要失衡的研究。斯特拉斯和夏皮罗的做法因为刻意消减筛检组中的高风险病人而授人以柄。国家乳房筛检研究犯了相反的错,即有选择地将高风险妇女归集到了筛检组,使得测验失衡。可想而知,他们的结论当然是负面的:相比于未筛检组,筛检组中反而有更多妇女死于乳腺癌。
☆☆☆
最后,这样的争议终于在瑞典平息。年冬天,我访问了马尔默这个20世纪70年代晚期瑞典乳房X射线摄影实验基地。它靠近瑞典半岛的最南端,坐落在毫无特色的灰蓝色风景之间,是一个宁静的灰蓝色工业小镇。斯科讷(Skne)省广袤贫瘠的平原延伸到它的北部,厄勒(resund)海峡环绕在它的南部。70年代的经济衰退严重击垮了马尔默,这个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在近二十年里陷入停滞,城市的迁入迁出率令人惊讶地萎缩到不足2%。马尔默这个被遗忘之地,羁縻着男男女女,构成了无法逃离的队列,实在是进行这种困难重重的实验的理想之地。
年,共有4.2万名妇女加入了马尔默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项目。其中一半人(约2.1万名妇女)医院外的小诊所进行一次筛检,另一半则不进行检查,从那时起,两组人就被密切地追踪观察。实验像时钟一样准确地进行着。“整个马尔默只有一家乳房诊所,这对于它的城市规模来说并不常见,”首席研究员英瓦尔?安德森(IngvarAndersson)回忆说,“所有的妇女一年又一年都在同一家诊所进行筛检,因而研究活动高度一致,尽在掌控之下,这是最能令人信服的一次实验。”
年年底,马尔默实验到了第12年,它公布了结果。总体而言,筛检组中有位妇女被检出乳腺癌,对照组中是位,这再一次揭示了乳房X射线摄影对于早期癌症的侦测能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第一眼看来,提早发现并没有拯救大量的生命。名妇女死于乳腺癌,其中63位在筛检组,66位在对照组,这在统计学上并没有明显区别。
但是在这些死亡病例后面,却浮现出一种模式。当对两组人进行年龄分析时,发现55岁以上的妇女中,乳腺癌的死亡率下降了20%,她们从筛检中受益。相比之下,在更年轻的妇女群体中,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没表现出明显益处。
这种在老年妇女身上益处明显、在年轻妇女中则难以察觉的模式,在追随马尔默实验的数十个实验中得以证实。年,也就是马尔默实验发起的26年后,一份汇集了瑞典所有实验的详尽的分析报告发表在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总计24.7万名妇女参与了实验,汇集分析(pooledanalysis)证明了马尔默结果的正确性。在15年的实验进程中,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使55岁到70岁的妇女的乳腺癌死亡率总计下降了20%到30%。但对于55岁以下的妇女而言,益处几不可察。
简而言之,乳房X射线摄影术,并不是乳腺癌妇女的真正救星。就像数据学家唐纳德?贝瑞(DonaldBerry)描述的那样,它的效果“对于某些妇女而言是无可争辩的,但同样其效果之有限也是无可争辩的”。贝瑞写道:“筛检就像买彩票。赢家总是少数妇女……绝大多数妇女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但是她们要花费时间,承担着筛检的风险……50岁之后没有做乳房X射线摄影筛检的风险就像是不戴头盔骑15个小时的自行车一样。”如果全国的妇女都选择不戴头盔径直骑车15个小时,当然会比起戴着头盔有更多的死亡。但是对于一周一次不戴头盔骑车去街角杂货店的妇女而言,她的风险根本就无足挂齿。
不过至少在马尔默实验中,人们并没有轻视这种细微的差别。原来的筛检组中,很多妇女已经死于各种原因,但是,就像一位当地居民形容的,乳房X射线摄影术“已经像是这地方的一种宗教信仰了”。一个冬日的清晨,我迎风站在门诊部外,看到成群的妇女(有些大于55岁,有些很明显要年轻得多)虔诚地走来接受她们一年一度的X射线检查。我想,这个诊所仍然在以它曾经的效率和勤奋运转着,在其他城市糟糕的实验尝试后,该城严格地完成了癌症预防史上最具潜力也最为困难的实验。病人们轻轻松松地进进出出,就像是午后例行公事一样。其中很多人骑着自行车,显然不顾贝瑞的警告,她们都没有戴头盔。
☆☆☆
为什么一个简单易学、便于纠正、经济实惠又对技法要求不高,而且可以觉察出乳房小型肿瘤阴影的X射线技术,要挣扎50年,经过了9次实验,才可以发现其益处?
部分原因是早期检查实验的复杂性,因为早期的实验总是难以琢磨、充满争议又容易出错。爱丁堡实验因为随机性的瑕疵而毫无结果;乳腺癌筛检示范项目则因非随机操作而失败。夏皮罗的实验因为过度追求客观而失败;加拿大的实验则因同情而功亏一篑。
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过度诊断和诊断不足这一固有的难题,尽管这中间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乳房X射线摄影术不是检查早期乳腺癌特别好的工具。它的假阳性和假阴性比率,使其远不能作为理想的筛检方法。但是,乳房X射线摄影术最致命的缺陷在于:这些比率并不绝对,它们取决于年龄。对于乳腺癌高发的55岁以上妇女而言,一个相对低劣的筛检工具就足以发现早期肿瘤并提供有益的帮助。对于40岁到50岁的妇女而言,乳腺癌的发生率下降到了一个程度,以至于乳房X射线检查所探明的“肿块”往往是假阳性。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被设计用来使小号字易辨的放大镜,当文字是10号甚至是6号时,可以出色地工作。但是当文字小到某个特定值、某个特定字号时,正确读出与犯错的概率等同。在55岁以上的妇女中,乳腺癌发生率的“字号”足够地大,乳房X射线摄影能发挥适当的作用。但是在40岁到50岁的妇女中,乳房X射线摄影处在一个尴尬的临界点,要眯起眼睛努力看——而这已超过了它的内在灵敏度,以致无法辨识。不管我们对这组妇女做多么密集的乳房X射线测试,它依旧是一个低劣的筛检工具。
当然最后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如何想象癌症和筛检。我们是视觉动物,相信眼见为实;我们也认为,能够看到癌症早期、刚出现的形式,就是阻止它的最好时机。就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Gladwell)曾经描述的,“这是一个教科书样板,抵抗癌症的战役就该照此进行。使用功能强大的照相机,摄取详尽的照片,对肿瘤进行涂片,越早越好。及早进行有力的治疗……肿瘤的威胁被可视化了。大就是坏,小就是好。”
然而即使照相机非常清晰给力,癌症还是挫败了这条简单规则。因为乳腺癌转移是致病人死亡的罪魁祸首,那么发现并移除转移前的肿瘤能够拯救妇女们的生命应该是对的。但是同样正确的是:肿瘤小并不意味着它还没有转移。即使几乎不能被乳房X射线摄影术检查到的小肿瘤,也可能携带令其大规模转移的基因组。相反,大肿瘤可能基因就是良性的——不太可能侵袭和转移。换而言之,肿瘤的大小,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已。肿瘤行为的差异不只是量变也是质变的结果。
静态图片很难捕捉到这种质的成长。发现一个“小”肿瘤,然后把它从身体里切除,并不能确保我们摆脱癌症,这是我们仍然在挣扎着不愿意相信的事实。毕竟,乳房X射线摄影或是巴氏涂片,都是对癌症初期的画像,就像所有的画像一样,它被期待着抓住这个主体的某些本质:其精神、内在、未来和行为。艺术家理查德?埃夫登(RichardAvedon)喜欢说:“所有的照片都是准确的,但没有一个是真相。”
☆☆☆
但如果每一种癌症的“真相”都已刻画到了它的行为中,那么人们要怎样才能捕捉到这种神秘的特质呢?科学家们怎样才能做出关键性的转变——从简单地看见癌症,过渡到知道其恶化的潜能、它的弱点、它传播的方式,以及它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晚期,癌症预防的整个学科受阻于这个关键所在。这个难题欠缺的一环就是对癌变的更深层次理解,即对正常细胞转变为癌细胞的机制的解释。在肝炎的慢性炎症中,乙型病毒和幽门螺杆菌发起了癌变的进程,但是,是通过什么路径?埃姆斯测试证明了诱变性与癌变相关,但是是哪些基因的突变?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呢?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突变,能否用它来创造出更智慧的方法来预防癌症?例如,是否可以不再进行大规模乳房X射线摄影实验,而通过更灵巧的摄影筛检对妇女进行风险分级,(检查出使人易患乳腺癌的突变)对高风险妇女进行更高程度的监测观察?这样的策略辅以更好的技术,会不会比简单的静态图像能更准确地捕捉到癌症的特性?
癌症的治疗似乎也进入了同样的瓶颈。哈金斯和沃波尔已经证明,理解癌细胞的内在机制能够揭示其独有的弱点。但是这一发现得由下而上进行:从癌细胞到其治疗。国家癌症研究所癌症治疗部前主任布鲁斯?凯伯纳(BruceChabner)回忆说:“这个十年结束之际,整个肿瘤学科,包括预防和治疗,似乎都撞到了知识的基本边界。我们在不了解癌细胞的情况下努力地对抗癌,这就像不懂得内燃机却要发射火箭一样。”
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说。在筛检实验举步维艰,致癌物逍遥法外,对于癌症机制的理解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急躁地部署大规模治疗性攻击的心情演变成了四处布设的易爆点。化疗药物就是毒药,人们并不需要理解癌细胞就可以对其下毒。所以,就像一代根除性外科医生曾拉下周围的百叶窗,让人不忍卒读地将这一学科推进到其可怕的极限,一代根除性化疗医师也这样做了。如果身体里每一个分生的癌细胞都被清除才能摆脱癌症,那就这样去做!——这个信条,将肿瘤学拖入了它最黑暗的时期。
①这种钙化点后被放射科医生称为“盐粒”。
②除乳房X射线外,妇女们也接受来自外科医生的附带常规乳房检查。
实体瘤自体骨髓项目①
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
——《圣经?撒母耳记》二十二章四十三节
癌症治疗就像是拿着棍子打狗,赶尽狗身上的虱子。
——安娜?迪佛?史密斯(AnnaDeavereSmith),
《让我静下来悲伤》(LetMeDownEasy)
2月是我最痛苦的一个月。进入年的第二个月份,迎接我的是一连串的死亡和旧病的死灰复燃;每一个病例都好像冬日里精准清脆的枪声让人震惊。36岁的史蒂夫?哈蒙(SteveHarmon)的胃的贲门处长了食道癌。他已经在化疗中苦苦支撑了六个月,像是陷入了希腊神话里惩罚的怪圈中。化疗带来的严重呕吐,是我从未在其他病人身上见过的,将他折磨得虚弱不堪。但他又必须不停地进食以防止体重下降。一周又一周,肿瘤不停地侵蚀着史蒂夫,他已经荒唐地开始对体重斤斤计较,要以盎司为单位来计量体重,仿佛生怕会忽然降到零而完全消失。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来陪伴他:一天早上,三个孩子带着游戏和书本来看望他,看着父亲不停地打着寒战,心里难以承受;他的一个兄弟满脸狐疑地转来转去,责备地看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用药给史蒂夫来阻止呕吐;史蒂夫的妻子,勇敢地带领全家经历着整个过程,好像是一次灾难性的家庭旅行。
一天早上,史蒂夫独自坐在输液室的躺椅上,我走上前问他是否更愿意一个人在单人间进行化疗,或许目睹化疗过程对他的家人和孩子来说太过残酷?
他有点恼火地望向别处。“我知道统计数字。”他的声音绷得紧紧的,像是被勒住了喉咙一样,“如果是我自己,我连试都不会试,我这样做,全是为了孩子们。”
☆☆☆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CarlosWilliams)曾经写道:“一个人的死,是因为死亡首先占据了他的想象。”就在那个月,死亡掠夺了我病人的想象,而我的任务是将他们的想象从死亡那里重新夺回来。这个任务难得无法形容,是一个远比派药和外科手术更玄妙和复杂的过程。用虚假的承诺夺回想象很简单,但要用微妙的真相来争取就难得多,它要求精细地测量再测量,谨慎地为患者打气。鼓吹太多的“恢复”和想象可能会膨胀为错觉,太少又可能会将希望一起掐灭。
苏珊?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DavidRieff)在记录母亲疾病的悲伤回忆录中,描述了桑塔格和一名卓有成就的医生在纽约的一次会面。从子宫癌和乳腺癌中幸存下来的桑塔格,被诊断出患有骨髓异常增生,这种尚未发展为癌症的疾病,常常会导致爆发性的白血病(桑塔格的骨髓异常是由于治疗其他早先癌症而接受的高剂量化疗所致)。里夫书中所称的A医生非常悲观,直截了当地告诉桑塔格完全没有希望。不仅如此,除了等待癌症在脊髓爆发外,没有任何对策,所有的选项都向她关闭了大门。医生的话就是宣判词,最终的、不可改变的一锤定音。里夫回忆说,“像很多医生一样,他和我们说话像对孩子一样,却没有考虑到一个通晓事理的成年人在对孩子说话时应注意的措词。”
这种毫不妥协的口气和傲慢自大的死刑宣判,对桑塔格几乎就是致命一击。特别是对于一个想要以两倍于常人的热情来拥抱生活、以两倍于常人的速度来呼吸世界的女人而言,绝望意味着窒息,沉寂就是死亡。桑塔格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找到另一个态度平缓得多、更愿意和她进行心灵沟通的医生。当然,在标准的统计学意义上,A医生是正确的。变化无常且难缠的白血病终于在桑塔格的骨髓中爆发了,而且的确没有什么医疗方案。虽然桑塔格的新医生也明确地告诉了她同样的信息,但却没有熄灭她对奇迹的期盼。他接连为她实施了一系列治疗:从标准药物到试验性药剂,再到姑息性药品,巧妙地与死亡一步一步地周旋,但仍然无法阻止统计学上的宿命。
在我做研习员期间碰到的所有临床医师中,最精于此道的莫过于肺癌医生托马斯?林奇(ThomasLynch),我常常随他出诊。林奇相貌年轻,却有一头惊人的白发;同他一起出诊,就是一种对医学微妙之处的体验。比如一天早上,66岁的妇女凯特?菲茨(KateFitz)做完大型医院复诊,发现检查结果是恶性的。她孤单地坐在候诊室里,等着听接下来的消息,看起来恐惧得快要崩溃了。
我正要进去,林奇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拖进旁边的房间。他已经看过菲茨的扫描和报告。被切除的肿瘤的各项指标,都显示出极高的复发风险。但更重要的,他看到了菲茨在候诊室里恐惧的样子。他说,现在,她需要的是另一种东西——“复活!”他一边若有所指地说着,一边跨步走进了菲茨的诊室。
我观察着他如何让人复活。林奇强调过程重于结果,他轻描淡写地道出了那些惊人的大量信息,让人毫无察觉。林奇告诉菲茨肿瘤的情况,关于手术的好消息,问候她的家人,接着谈起他自己,谈起自己的女儿总是抱怨在学校沉闷的日子。“您有孙辈吗?”他问到,“儿子或是女儿有没有住在附近?”然后我注意到,他开始引入一些数据,手法让人叹为观止。
“您也许从别的地方知道了您的这种癌症,原位复发或是转移的可能性较高,”他说,“可能会高到50%到60%。”
她点点头,紧张起来。
“不过即使发生了,我们也有办法来照顾它。”
我注意到他说的是“即使发生”,而不是“如果它发生”。虽然那些数字说明了统计意义上的事实,但是他的话却有巧妙的差别。他说的是“我们也有办法”而不是“我们消灭它”。照顾而不是治愈。谈话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在他手里,这些信息是某种活动着的、熔化了的东西,随时准备着冷冻成型,既透明又可以商量;一边轻轻地推动,一边塑造它,就像玻璃师把玩手中的玻璃一样。
一个为自己身患Ⅲ期乳腺癌而焦虑的妇女,需要夺回一些想象才能接受可能延长生命的化疗。一位患有致命的抗药性白血病的76岁老人,正尝试着另一轮激进的试验性化疗,他需要一点想象力来接受无药可治的事实。艺术千秋,人生朝露(Arslonga,vitabrevis)。希波克拉底告诉我们,医术绵长,“生命短暂,时机易逝;冒险试验,判断有瑕。”
☆☆☆
对癌症治疗法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是特别残酷的年份,希望与失望相混杂,复原力与绝望相胶着。就像是医生作家亚伯拉罕?韦尔盖塞(AbrahamVerghese)所写,“如果说这是西方医学界一个不切实际、空前自信的时代,濒临在自负的边缘,还是太轻描淡写了……治疗结果不好,是因为患者年纪太大,体质虚弱,或者是病人就医太迟。总之,从来不是因为医学无能。”
“似乎没有什么是医学不能做的……外科医生,如汤姆?斯塔泽(TomStarzl)……正在进行12到14个小时的‘集群手术’,肝、胰脏、十二指肠、空肠被整体从捐赠者体内取出,移植到原本满是癌细胞、如今被清空以备接受这些器官的病人的腹内。”
“斯塔泽是那个时代医学的偶像,在前艾滋病时期,每隔一晚就有一次被急诊叫到阵地前沿。”然而被挖空和移植了“器官花束”的病人并没有活下来:他们从手术中幸存下来,但仍死于癌症。
与外科攻击癌症的“掏空病人身体,再进行移植”所对等的化疗方式,被称为同种骨髓移植(AutologousBoneMarrowTransplant,简称ABMT)。它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起了美国和国际的白颠的危害白颠的危害